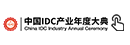2021年,互联网领域仍将成为反垄断的执法重点,会出现一批重要案件,而新《反垄断法》的出台将是2021年反垄断领域值得期待的大事。
“反垄断”成为近期中国经济的热词,并不断出现在高层会议中。
继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“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,一周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这一重要工作,要求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、数据收集使用管理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。
同时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据《反垄断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等查处多起涉及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案件,引起广泛关注。
对于在2021年必将继续“热”下去的“反垄断”,第一财经专访了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光耀。
许光耀教授从事《反垄断法》研究二十余年,是我国最早开始《反垄断法》研究的学者之一。他认为,2021年,互联网领域仍将成为反垄断的执法重点,会出现一批重要案件,而新《反垄断法》的出台将是2021年反垄断领域值得期待的大事。

互联网领域将成为反垄断重点
第一财经:2020年末,从政策和案件宣判上都表明反垄断的力度在不断加强,您认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如此大力地反垄断?
许光耀:一方面原因是,互联网产业属于新兴产业,在本世纪才得到相对较快的发展。发展初期,由于市场空间广阔,经营者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尽快占据这些空间,发展过程中展示的多为正面效应。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,继续发展的空间减少,就出现用垄断行为来限制竞争、谋取利益,随着这类行为越来越多,互联网领域也将成为新的执法重点领域。
另一方面原因是,在《反垄断法》实施初期,由于互联网业态的运行方式尚未充分展开,对其中各种垄断行为的规律不太容易把握,而全世界《反垄断法》理论研究与实务中都存在这一问题。因此,各国实际发生的执法与诉讼案件都不多,但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保持着对这一领域的关注,持续进行着各种角度的研究。
在这些探索过程中,一些重要案件成为全世界《反垄断法》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,人们对互联网领域双边市场的界定标准、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、竞争效果的分析方法等问题的认识有了长足的推进。
在《反垄断法》实施之初,大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,“对新兴产业要审慎监管,要保持《反垄断法》的谦抑性”,以免不当的监管本身会对效率造成损害,反而有违反《反垄断法》的初衷。但今天这一说法不再是适当的了。从目前来看,互联网行业的垄断行为已经充分展示出其危害性,妨碍着该产业的良性发展,《反垄断法》应当加大作为,而不是刻意地去谦抑。
第一财经:近期有几个处罚案例,包括三起并购案受到市场监管总局处罚,VIE结构不再成为互联网企业逃避反垄断申报理由;京东、天猫、唯品会因在2020年“双11”前后等不正当价格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处罚;对“二选一”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。您认为目前这些反垄断处罚重点打击哪些情况?
许光耀:接下来打击的重点将会是互联网领域的垄断行为。中国反垄断执法有一个特点,即某个时期在查处某个案件比较成功后,会借取得的经验继续针对这一领域加强重点执法,比如原料药、汽车领域都曾是《反垄断法》查处的重点。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已有经验的“规模效应”,提高执法效率。
因此在未来几年内,互联网领域也将会成为反垄断执法的重点查处领域。对互联网的规律经过长期执法和长期摸索后,执法机构对法理和规则有了更深入的理解,很可能在这一领域尽可能高效率地集中查处一批案件。而且互联网领域的垄断行为类型可能会更多,也更复杂。
第一财经:互联网巨头深入社区团购市场,也受到了政策的关注,您认为这其中会产生哪些垄断问题?
许光耀:《反垄断法》需要关注的是,互联网企业进入社区团购时,是不是从事了掠夺性定价行为,需要查处的是掠夺性定价行为,而不是市场进入本身。

掠夺性定价行为的运行分为两个阶段:在第一阶段,行为人把价格降到成本以下,以扩大自身亏损的方式,迫使竞争者亏损;在使竞争者退出市场后,行为人将进入第二个阶段,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,不仅收回掠夺的成本,而且获得高于竞争性水平的利润。其中,第二个阶段才是行为的目的。
我国《反垄断法》第17条有明确的规定:“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:……(二)没有正当理由,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;……”当然,对于该条的适用方法,还应以配套立法作必要的补充,而不能简单套用条文的字面含义,尤其是对掠夺性定价行为适用第17条还有一个理论障碍:总体说来,掠夺性定价是形成支配地位的方式,而不是对既有支配地位的利用方式。
而第17条第2项的适用以行为人拥有支配地位为前提,从而产生逻辑上的“鸡蛋相生”的悖论:在当事人价格低于成本时,它尚未拥有支配地位;而当其通过掠夺获得支配地位后,它的价格又不再低于成本。要消除这一矛盾,建议对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支配地位认定标准作进一步的阐释。
《反垄断法》修订或在2021年完成
第一财经:您认为今年反垄断领域还会发生什么大事?
许光耀:首先,2021年反垄断领域应当会出现一批重大案件;其次就是《反垄断法》的修订。2020年初,《反垄断法》修法就完成了征求意见阶段,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审议,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消息,《反垄断法》在2021年预安排的重点立法工作之内。
我认为,《反垄断法》的修订或将加速,有望在2021年推出,其配套立法也将更加全面,包括《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(征求意见稿)》(下称《反垄断指南》)也可能出台,互联网领域执法力度会加强。
第一财经:《反垄断法》和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有何侧重和不同,如何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?
许光耀:《反垄断法》和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有很大区别,《反垄断法》侧重维护竞争的自由,而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侧重维护竞争的公平;《反垄断法》维护市场的竞争性,即竞争性的市场结构,而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则侧重维护竞争者。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秩序。
具体而言,《反垄断法》所调整的各种垄断行为的目的,都是通过对竞争活动的限制,形成或维持市场力量,即“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的能力”。比如,竞争者互相构成对方提高价格的阻碍,于是达成垄断协议,消除彼此间的竞争,从而共同形成提高价格的能力。之所以对垄断协议进行管辖,是因为它带来提高价格的可能性,而提高价格将导致产出减少,损害效率。
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维护的是竞争的公平性,针对的是假冒伪劣、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,对过度的、无序的竞争进行制止,从而形成公平的竞争,与市场力量没有关系。
2017年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修订时,增加了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,对经营者实施恶意不兼容等行为进行规制,与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相互配合,分别从禁止不正当竞争和禁止限制竞争的角度,规范市场竞争秩序,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。但仅仅增加条款还不够,还需要为“恶意”的评价提供必要的标准与方法。
第一财经:《反垄断法》自2008年8月1日施行起,已经实行了超过12年,也需要根据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进行修改。2020年,《反垄断法(修订草案)》也完成了公开征求意见,您认为《反垄断法》修订会有哪些亮点?对《反垄断法》的修订有哪些建议?
许光耀:《修订草案(征求意见稿)》关注互联网领域,首次增加了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条款,认定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还应当考虑网络效应、规模经济、锁定效应、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。这有助于宣示对互联网领域的重视。但仍然需要对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与方法进行更详细的阐释,才能为网络效应、规模经济等的考察方法提供必要的指引。
此外,《反垄断法》的修订中最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,是效率和竞争的关系问题,也就是《反垄断法》的立法目的问题。
《反垄断法》本质上并不是维护竞争的法律,而是促进效率的法律。竞争性市场结构下,竞争者无力提高价格,只能通过扩大产出的方式来增加利润,因而是增进效率的;但有些情况下,对竞争施加必要的限制反而能导致产出增加,这时则应以效率为重,对这些竞争限制予以允许,而不是片面地为了维护竞争而维护竞争。所谓效率,包括产出大化与创新加速两种类型,前者称为静态效率,后者称为动态效率。
《反垄断法》第15条规定了垄断协议的豁免条件,包括为改进技术、研究开发新产品的;为提高产品质量、降低成本、增进效率,统一产品规格、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等7项。
这一规定难体会这七类豁免理由之间的关系。在欧盟法上,将效率统称为“促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,或促进经济与技术进步”,即包括“产出效率”与“创新效率”两种类型,中国《反垄断法》的第15条也可以采用这种概括方法,而不是采用上述列举式,后者不仅有所遗漏,甚至还会有错误。
比如企业间如果在规格上存在竞争,则统一规格的协议便可能构成垄断协议,是受审查的对象本身,而不是豁免的理由。因此第15条中“统一产品规格、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”应当删除。
第一财经: 2020年11月10日,市场监管总局发布《反垄断指南》,您认为这部指南将产生什么作用?
许光耀:《反垄断指南》将成为互联网行业反垄断合规的指导性文件。《反垄断法》加《反垄断指南》的组合拳表明监管机构要对互联网企业加强执法的态度,也给企业一个警钟。
但指南的一些表述也需要进一步完善。如《反垄断指南》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对“二选一”行为的否定态度。“二选一”是个通俗的说法,其在《反垄断法》上的术语化表达是“排他性交易”,包括排他性购买与排他性销售两种类型。排他性交易有可能构成支配地位滥用行为,有可能成为垄断协议的工具,也有可能并不构成垄断行为,具体属于哪种情况,应依据个案案情来认定,需要证明其满足垄断协议或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要件。
同时,排他性交易有时可以产生防止搭便车、防止套牢、维护产品与企业形象的统一性等效率后果,即使构成垄断行为,如果是实现这些效率所必需的,也通常可以合法。因此排他性交易并非一概应予禁止。指南的内容应当更细致一些才好。